“窮年憂黎元,嘆息腸內熱。”全詩意思,原文翻譯,賞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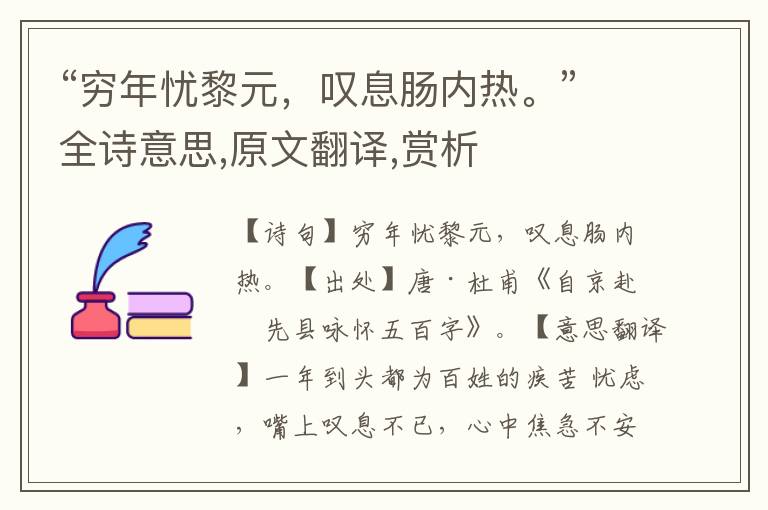
【詩句】窮年憂黎元,嘆息腸內熱。
【出處】唐·杜甫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》。
【意思翻譯】一年到頭都為百姓的疾苦 憂慮,嘴上嘆息不已,心中焦急不安。 窮年:整年,終年。黎元:百姓。腸內 熱:內心焦急不安。
【用法例釋】用以形容時時為人民 的疾苦憂心忡忡。[例]他的作品直面 人生、披肝瀝膽、大氣磅礴。他憂時、憂 世、憂濟元元的激情洶涌激蕩其中,他 的“窮年憂黎元,嘆息腸內熱”的精神, 充溢字里行間。(兆騫《我眼中的梁曉 聲》)
【賞析】盡我一生,都為天下蒼生擔憂不已,一想到他們受苦受難,自 己心里就像火燒似地焦急。孟子說:“禹思天下有溺者,猶己溺之也,稷思 天下有饑者,猶己饑之也,是以若是其急也。”此句詩歌中,杜甫明顯以稷 契自比,一想到百姓受苦,他自己內心就焦急難耐,所以才說“窮年憂黎 元”。他窮盡自己一生,要與天下百姓同甘共苦,衷腸熱烈如此,憂國憂民 如此!他的這種悲天憫人的情懷為后世贊嘆不已,故后人常用此句表達 憂國憂民的思想。
【全詩】點擊進入
【題解】
唐詩篇名。五古。杜甫作。見《杜詩詳注》卷四。天寶十四年(755)十月,杜甫被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,十一月,離長安赴奉先(今陜西蒲城)探望家室,此詩為到家后所作。全詩五百字,可分為三段:首段自述生平大志,抒寫憂國憂民懷抱;二段敘述途經驪山時的所見所聞,抒發社會不公之感慨;三段敘寫到家后情形,由幼子餓卒的家庭悲劇聯想至百姓的困苦。詩中無情揭露統治階級上層集團的荒淫奢侈,深切表現對人民疾苦的同情,為詩人長安十年政治生活之總結。其時安史之亂已爆發,只消息還未傳至奉先,但時弊叢生,危機四伏,動亂將至的社會現實和時代氣氛在詩中得到深刻反映。該詩是杜集中長篇詩史式作品之一。詩題為“詠懷”,實則集詠懷、紀行、紀事于一篇,熔議論、敘事、抒情、寫景于一爐,全篇間架宏闊,波瀾浩瀚,蔚為壯觀,且百折千回,仍復一氣流轉,極反復排蕩之致。邵長蘅評曰:“《詠懷》、《北征》皆杜集大篇,子美自許沉郁頓挫,碧海鯨魚,后人贊其鋪陳排比,渾涵汪茫,正是此種。”(《唐宋詩舉要》卷一引)楊倫亦云:“五古前人多以質厚清遠勝,少陵出而沉郁頓挫,每多大篇,遂為詩道中另辟一門徑。無一語蹈襲漢魏,正深得其神理。此及《北征》,尤為集內大文章,見老杜平生大本領,所謂‘巨刃摩天’、‘乾坤雷硠’者,唯此種足以當之。”(《杜詩鏡銓》卷三)“窮年憂黎元,嘆息腸內熱”二句,自陳愛國憂民之心,感人肺腑;“朱門酒肉臭,路有凍死骨”二句,針砭貧富懸殊社會現象,“驚心動魄”(趙翼《甌北詩話》卷二),均為傳誦千古的名句。
【評論】
詩歌篇名。唐杜甫作。宋張戒《歲寒堂詩話》:“少陵在布衣中,慨然有致君堯舜之志,而世無知者,雖同學翁亦頗笑之,故‘浩歌彌激烈’,‘沈飲聊自遣’也。此與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無異。讀其詩,可以想其胸臆矣。嗟夫!子美豈詩人而已哉!其云:‘彤庭所分帛,本自寒女出。鞭撻其夫家,聚斂貢城闕。圣人筐篚恩,實欲邦國活。臣如忽至理,君豈異此物。多士盈朝廷,仁者宜戰慄。’又云: ‘朱門酒肉臭,路有凍死骨。榮枯咫尺異,惆悵難再述。’方幼子餓死之時,尚以常免租稅、不隸征伐為幸,而思失業徒,念遠戍卒,至于‘憂端齊終南,’此豈嘲風詠月者哉,蓋深于經術者也。與王吉、貢禹之流等矣。”宋黃徹《?溪詩話》:“觀《赴奉先詠懷》五百言,乃聲律中老杜心跡論一篇也。自‘杜陵有布衣,老大意轉拙。許身一何愚,竊比稷與契。’其心術所向,自是稷契等人;‘窮年憂黎元,嘆息腸內熱。’與饑渴由己者何異,然常為不知者所病,故曰‘取笑同學翁。’世不我知,而所守不變,故曰‘浩歌彌激烈。’又云:‘非無江海志,蕭灑送日月。當今廊廟具,建廈豈云缺。葵藿傾太陽,物性固莫奪。’言非不知隱遁為高也,亦非以國無其人也,特廢義亂倫,有所不忍,‘以此誤生理,獨恥事干謁。’言志大術疏,未始阿附以借勢也。為下士所笑,而浩歌自若,皇皇慕君而雅志棲遯,既不合時而又不少低屈,皆設疑互答,屢致意焉。非巨刃有余,孰能之乎?中間鋪敘,間關酸辛,宜不勝其戚戚而‘默思失業徒,因念遠戍卒。’所謂憂在天下,而不為一己失得也。禹稷、顏子,不害為同道;少陵之跡江湖而心稷契,豈為過哉!孟子曰:‘窮則獨善其身,達則兼善天下。’其窮也未嘗無志于國與民;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,蚤謀先定,出處一致矣。是詩先后周復,正合乎此。昔人目元和《賀雨詩》為諫書,余特目此詩為心跡論也。”清浦起龍《讀杜心解》:“是為集中開頭大文章,老杜平生大本領。須用一片大魄力讀去,斷不宜如朱、仇諸本,瑣瑣分裂。通篇只是三大段。首明赍志去國之情,中慨君臣耽樂之失,末述到家哀苦之感。而起首用‘許身’、‘比稷、契’二句總領,如金之聲也。結尾用‘憂端齊終南’二句總收,如玉之振也。其‘稷契’之心,‘憂端’之切,在于國奢民困。而民惟邦本,尤其所深危而極慮者。故首言去國也,則曰‘窮年憂黎元’;中慨耽樂也,則曰‘本自寒女出;’末述到家也,則曰‘默思失業徒’。一篇之中,三致意焉。然則其所謂比‘稷、契’者,果非虛語;而結‘憂端’者,終無已時矣。”清楊倫《杜詩鏡銓》:“首從詠懷敘起,每四句一轉,層層跌出。自許稷、契本懷,寫仕既不成,隱又不遂,百折千回,仍復一氣流轉,極反復排蕩之致。次敘自京赴奉先道途所聞見,而致慨于國奢民困,此正憂端最切處。末敘抵家事,仍歸到憂黎元作結,乃是詠懷本意。”“五古前人多以質厚清遠勝,少陵出而沉郁頓挫,每多大篇,遂為詩道中另辟一門徑。無一語蹈襲漢魏,正深得其神理。此及《北征》,尤為集內大文章,見老杜平生大本領;所謂巨刃摩天,乾坤雷硠者,惟此種足以當之。”此詩作于唐玄宗天寶十四載(755)冬,時安祿山已反于范陽,但消息尚未傳到長安,而玄宗與貴妃仍宴游于驪山。作者回家探親,途經山下,感念國事,憂憤交集,到家后寫下此詩。通過描述個人的身世遭遇和路途見聞,抒發了往昔的壯懷,當前的慨嘆和對國事的憂慮;揭露了統治集團醉生夢死、窮奢極欲、橫征暴斂的罪惡,真實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夕尖銳的階級對立和危機四伏的政治形勢。全詩夾敘夾議,鋪陳始終,將敘事、抒情、議論三者結合起來,表達百轉千回、波瀾起伏的思想感情,構成了“沉郁頓挫”的藝術風格;命意布局嚴謹,圍繞抒寫壯志、憂慮國事這個中心,或記所見,或敘所聞,或述所感,雖內容豐富,但脈絡清楚,結構完整;成功地運用對比手法,形象鮮明,生動感人,“朱門酒肉臭,路有凍死骨”一聯,集中地深刻地揭示了階級的對立,具有驚心動魄的藝術力量,明盧世?說:“《赴奉先》及《北征》,肝腸如火,涕淚橫流,讀此而不感動者,其人必不忠”(清仇兆鰲《杜詩詳注》引)。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