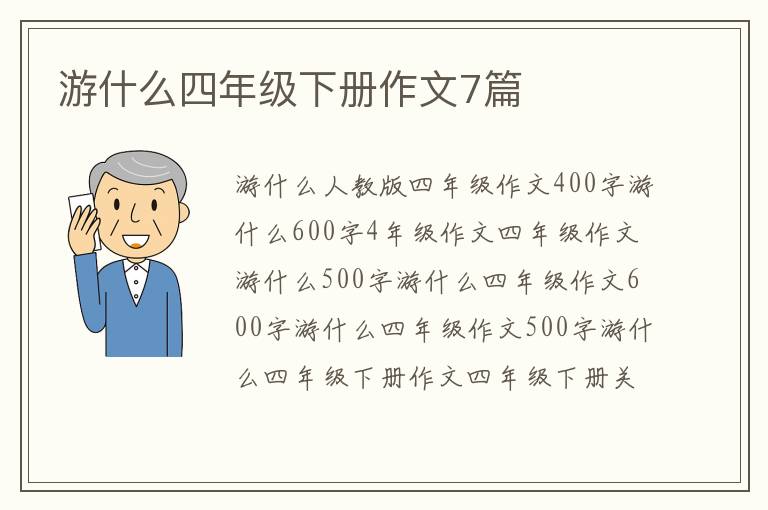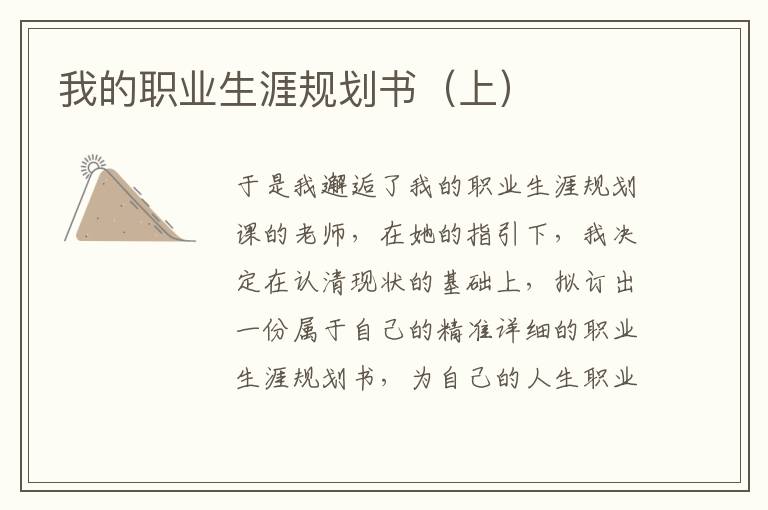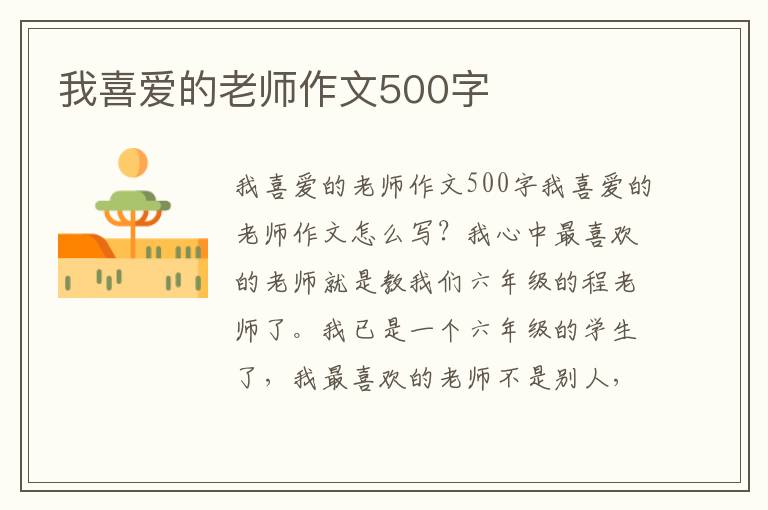演戲作文1600字

上大學的時候真是瘋。我們這些七七、七八級的學生在考進北大之前,大都已經在社會上滾了許多年,手上厚厚的繭子,臉上淡淡的皺紋,可那童心就像久被關在瓶子里的魔鬼,一放出來,膨脹得可怕。讀書要拼命,玩起來也要拼命。什么野炊啦,自行車旅游啦,辦刊物哇,搞文學社呀,鬧騰得很。到了大學三年級,我們突然決定,要演戲了。 記不起誰最先提起這個事的。好像是校學生會來了個干事,說年底要進行北京市高校學生話劇匯演,問我們誰會演戲。演戲有什么會不會的,不就是敢不敢上臺的問題嗎。我們回答得很沖。兩年多的大學生活,中文系文學專業的學生已經在全校出了名,外面光傳我們中間有多少多少能人,多少多少才子,連出小戲都演不了,不叫人笑話啦。再說,演戲本身是件極新鮮,極熱鬧,極開心的事呢。 聽說我們要演戲,好多人給我們送來他們寫的劇本。我們選來選去都沒有太中意的,只得先定下兩個,一個叫了海濱來客》,是外系學生寫的,一個叫《美麗的愛情》是班里同學李春寫的。
《海濱來客》講的是一位部長的女兒到某海濱她父母舊日的老部下家中度假。消息被一伙匪徒得知,他們擬定了一個劫持計劃。女匪首親自出馬,化裝成部長女兒的模樣,同時出現在那個老部下的家中,兩個姑娘真假難辨,鬧出一連串荒唐、滑稽的笑話。我演真的部長女兒,黃蓓佳演那個假的,由于臺詞寫得不甚合意,我們決定每個演員根據情節即興創作。結果,到了正式演出,每演一場,臺詞都有一定的變動,這隨機應變而產生的火花,常給人妙語橫生的感覺,逗得觀眾樂不可支。記得當時觀眾最喜歡劇中那個警察的角色。他是由新聞專業的楊迎明扮演的。楊迎明很壯實,高身量,黑而胖,穿上一身警服,歪戴帽子,一口地道的京腔兒加俏皮話,一舉手一投足活像個國民黨兵痞。只要他張嘴說話,臺底下便拍手跺腳,反應極其熱烈。就連其他演員也常被他弄得忍俊不已。
演戲是最忌“笑場”的,萬一哪個演員在關鍵情節“撲味”笑出聲,買賣就砸了。所以我們不止一次警告楊迎明“悠著點兒”。不過這也真不容易,甚至挺痛苦。比方說戲演到尾聲,有一情節要求女匪首掏出手槍對眾人進行誘惑、恐嚇。我們每每看到黃蓓佳摸著一把玩具手槍張牙舞爪,心里都笑岔了氣,只好拼命忍住,堅持到大幕拉上,才抱著肚子滾倒在臺子中央。《美麗的愛情》也是部小喜劇,角色大都是由我們班上的同學扮演的。演員演得很松弛,本子的生活氣息也較濃,所以劇場效果相當不錯。這兩部戲連演了一個星期,場場“爆滿”,我們都很得意。 好在我們并沒有被初步的勝利沖昏頭腦。
我們明白,這兩部戲僅僅流十“鬧”的形式,演員開心,觀眾也開心,其他方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 班扭腸拼犯妞扮翻口且婦抓且月翻具演戲面卻幼稚得很。真要把這種戲推上去參加大學生匯演,未免 “丟份”。正當我們愁得厲害的時候,班里同學陳建功自告奮勇,答應專門為我們寫個本子。 陳建功在學校可是有名人物,小說寫得好,全國得獎,為人又穩重。他曾搞過話劇、電影劇本,寫部獨幕劇,當然手到擒來。我們眼巴巴盼著,覺得那幾日他的表情格外嚴肅、認真。 劇本脫稿,名字叫“良心”。我們傳閱一遍,一致首肯。劇本反映的問題在當時看,是較尖銳的。 一個和睦的家庭。慈父嬌女,姐妹相愛。然而,這種溫馨氣氛卻因一位上訪的瞎老人的出現,被破壞了。老人是為自己二十多年前蒙冤而死的女兒上訪告狀的。面對瞎老人的哭訴,在某政府機構擔任領導職務的父親顯得神色惶惑,原來,他就是二十多年前制造那起冤案的元兇。能夠揭露這個事實的惟一證據,是老人女兒留下的一封信,圍繞著這封信,故事展開了 ……顯然,這個劇本的政治性很強,但它又不是生硬的說理,而是以情感人,所以具有相當吸引力。大學生的神經是最為敏感的,我們在創作沖動之余,深知這個劇本將在觀眾中引起什么樣的反響。 角色定一了。曾在《美麗的愛情》中扮演父親的劉志達,在這部戲里仍演父親,從沒演過戲,但渾身都是文藝細胞的李彤,承擔了瞎老人的角色,黃蓓佳演姐姐,我演妹妹。
排練沒有開始,學校里已經紛紛揚揚傳說七七級文學專業新搞的話劇如何如何。每次對臺詞,無論地點在哪兒,都有人趕來旁聽,弄得我們怪緊張的,也格外賣力。不過,對這個戲最上心的還屬陳建功。他是排練的必到者,核心人物,常對我們提出想法和要求,使我們對他的話不得不做深沉狀。為了增加我們的悟性,陳建功專門從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請了一位老導演給我們排戲。 老導演抱著胳膊坐在臺下,我們一段段地演給他看,不時被他叫停。“你應該這樣,這樣……”“應該自信,放松,認為專業演員也不如自己……”我們似懂非懂地點頭,可要立馬兒在這位真正的導演面前建立起超過專業演員的優越感來,還費點勁兒。那位導演對李彤的表演最感興趣。他叫住李彤,詢問李彤看過幾回話劇《茶館》。李彤答,七、八回吧。他點頭,稱李彤的表演活脫《茶館》里于是之的模樣。
我們細看,果然偷了《茶館》最后一幕里那位窮愁潦倒的老掌柜的形神,閉著眼聽,簡直可以以其之假,亂于是之之真。我們惋惜于是之沒能看我們排戲,不然,他定會為自己多了個傳人而高興。 戲排好了,貼出老大的海報。學校領導,學生會干部和許多中文系老師都來看我們的首場演出。辦公樓禮堂坐得滿滿的。我們從幕縫中偷偷向下瞥,心里的滋味竟和前幾次演戲大不一樣。音樂起,大幕緩緩拉開,我覺著我的腿肚子開始哆嗦了。戲演了一會兒,我發現“爸爸”和“姐姐”的情緒也都不那么正常。劉志達說著說著,竟然忘了回臺詞,急得我和黃蓓佳直眨眼睛。好不容易,握到假“于是之”上場了。他一露面,就跌跌撞撞地撲向劉志達,喊了聲“首長”。劉志達扶住他,說:“不要叫首長,叫同志吧。”“是人就是我們的首長啊!”李彤的話音剛落,臺下突然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。我們都惜了。來不及細想,仿佛打了針嗎啡,我們頓時來了精神。往下一切都順順當當的。一個個的自我感覺那份兒好,到劇終時,每個人都快演“瘋”了。臺下反應和我們一樣熱烈,幾乎隔不多久,便有一陣掌聲。演出結束后,我們走下臺,看到謝冕、陳貽掀、馬振芳等幾位中文系老師的眼里都嘀著熱淚。當然,還有我們的班主任張劍福,他平時最怕我們翹尾巴的,所以總敲打我們。
這回他卻講了許多鼓勵的話。 我們一共在學校演了四場。那幾天走到哪兒,都聽到有人議論我們的戲。 大學生話劇匯演的日子到了。我們一大早乘車來到中央戲劇學院。已經是十二月底,天氣相當冷。我們裹著大衣東跑西顛,打聽化妝室在哪兒?一共有多少學校參加匯演?評委是準?中午吃飯問題怎么解決?一切沒有明確答復,我們只好硬著頭皮進化妝室。因為占用的地盤大小和別的學校爭執了幾句;又因為把我們的戲排在靠后面,下午才能演,我們沖匯演工作人員嚷嚷起來。明知嚷沒用,可還想嚷幾句,仿佛這樣才能穩住神兒,心里才踏實。看看別的學校,不得不承認人家的氣派:全套的化妝用品,專業的化妝師還帶著電吹風。新做的行頭,衣服拎起來連個褶兒都沒有。布景是一流的,做道具用的豪華沙發得四、五個人抬。我們呢,衣服是家常的,布景只有一張方桌,兩把椅子。
往好里說,是現代派;往壞里想,是窮酸。 終于輪到我們上場,我們每個人都竭盡全力了,仍覺得效果沒有學校時好。謝了幕,我急著問陳建功,“怎么樣?’’“不錯,不錯。”聽他答話,我卻感到言不由衷。卸妝的時候,有兩個學校跑到后臺向我們要劇本。見他們那樣誠懇,我們才稍稍恢復了自信心。 匯演結束了,評選結果要待一個星期后揭曉。我們回到學校,面臨緊張的期末復習考試,一時也顧不了其他的事。可消息還是不斷傳來。聽說我們獲獎了,一等獎,有獎狀,有獎品。又聽說對我們這個戲有爭議,政治上太露骨,有人點頭,有人搖頭。后來,傳說電視臺要轉播我們的戲,我們都興奮一陣。等來等去音信渺茫,我們便涼下來。演戲畢竟是演戲嘛。 離開北大到出版社當編輯已經好幾年,經常天南地北地出差,免不了碰上幾個校友。知姓名的,面熟的是少數。可只要他們提一句“過去看過你演戲”,我心里總要“坪”地撞一下,好像是發生了感情共振,忍不住要抓住對方,親熱地“侃”一番:那時我們在北大如何如何……